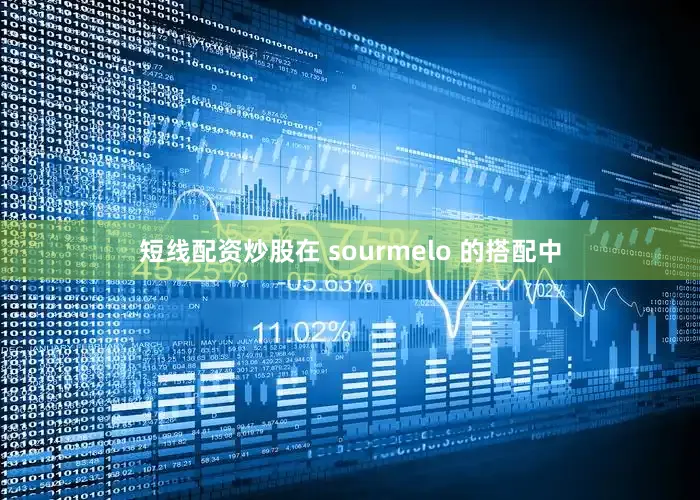每年6-8月,都是各家暑期档电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黄金时段。
2025年夏天,《长安的荔枝》让唐朝打工人李善德为了几颗荔枝累死累活,大银幕外的观众隔空和这个底层牛马深深共情了;浪浪山的小猪妖也在妖魔鬼怪界“对齐颗粒度”,历经千难万险一路西行;F1赛场上的布拉德·皮特风驰电掣,让多少小白热血沸腾地垂直入了赛车的坑。
即便有这些好评不断的作品,却依然没有拯救今年暑期档的惨淡。截至8月4日(档期第65天),总票房仅70亿出头,不仅和前年136.64亿的好成绩差距悬殊,也低于去年同期的82.48亿[1][2]。
就在一众叫好不叫座的电影中,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南京照相馆》却如“黑马”一般闯进大家视线。从商业表现来看,上映11天票房超16亿位列第一,为今年扑街的暑期档做了不少贡献。更重要的是,在豆瓣超25万人(8.7数据)参与的综合评价下,取得了8.6的评分[3]。
历史创伤题材,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难点。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表达的关系,是创作者必须面临的挑战。那么,在今年相对冷清的暑期档市场中,这部影片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关注?
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残酷
拍摄前,主创团队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实地探访的方式搜集信息,并按照老照片尽力还原南京的大街小巷、地标城墙,为的就是一个“真实”[4][5]。
所以电影一开始,当观众跟随邮递员苏柳昌(刘昊然饰)的视角,看到曾经熟悉的热闹繁华变得满目疮痍时,也会更沉浸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他们正在经历的,是家园的溃散与丧失。
在战争和屠杀这样“宏大”的背景下,影片自始至终却都围绕着一个“细小”的切口展开——照片。
电影讲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从日本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奉命拍摄战争影像为起点,冒充学徒的苏柳昌因需要冲洗底片意外得以保命,“多洗一天照片,就能多活一天”。然而,当底片内容从军官士兵的肖像逐渐转为血腥屠杀的真实记录时,躲在吉祥照相馆的一行人也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否要继续冲洗照片?又是否应该将它们完整保存并带出南京?

众人战战兢兢,其实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战争期间,无论是对本国随军记者,还是摄影师和作家,日本当局对任何有关“南京战事”的影像记录都会进行严格审查。就拿管控极为苛刻的战场实录为例: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每天将随军记者以航空寄回的照片加洗四张,送往各大情报局审批。带有“检阅济”印记的照片才能在报刊上发表,而盖上“不许可”的照片不仅无法刊登,连泄露都被严厉禁止[6]。《南京照相馆》中,伊藤的多张照片经历退回不予印发的过程,就是对这一史实进行的还原。
一边是报纸、信件、出版物均需要严格送审,稍有不慎就会没收或者删除,甚至有性命之忧;一边是以摆拍和捏造宣传南京城“一片祥和”[6][7]。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屠杀细节的影像保存下来,可想而知属于地狱难度。苏柳昌、老金(王骁饰)、林毓秀(高叶饰)等人,只能采用将底片缝入衣服这种“剑走偏锋”的危险方法,这些珍贵的记录才不至于烟消云散。
“暗中冲洗底片保留南京大屠杀影像”,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历史却远比艺术处理更残酷。
影片中的吉祥照相馆,原型为南京市区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时在店里当学徒的罗瑾无意中发现,日军少尉命其冲洗的底片包含大量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以及奸污女性的镜头。他暗中加洗了一套照片,并选择16张悄悄留存[8]。
起初,他将这套照片藏在照相馆暗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家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罗瑾几经辗转进入毗卢寺集训,面对宪兵突如其来的搜查,情急之下他只能将相册转藏在寺内厕所墙上的一个洞里。但几天后,照片竟然不翼而飞。罗瑾深知其中的危险,经历从南京到上海等多次逃亡,最终落脚到了福建大田县[8]。
实际上,是罗瑾的同学吴旋发现了墙洞中的相册并将其转移。这场“接力”,吴旋同样东躲西藏,同样心惊胆战,有次还在被发现的边缘命悬一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南京解放,南京临时参议会搜集日方罪证时,他才将这本令人提心吊胆六年之久的相册上交。审判谷寿夫等罪犯的过程中,16张照片被列为南京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8][9]。

这个启发主创团队的故事底色本就是令人揪心的。以南京大屠杀为基,以照片中记录的暴力和血腥为主线,让这部电影注定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电影”。观众观影时感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欣赏,而是和现实记忆交织在一起的历史重量。
事实上,这也是所有拍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战争题材,从记录到反思
如何呈现历史的伤痛,怎样面对观众的情绪,通过影像要传达什么样的观念……围绕这些主题,电影人其实已经探索了许多年。
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故事片《屠城血证》上映,这里的“血证”,指的正是和《南京照相馆》取材于同一历史事件的相片集[10][11]。影片的主线剧情,也由保护照片的医生展涛、照相馆老板范长乐等人展开[10]。但和后者选择的小切口视角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更侧重于展现历史事件真实情况,并穿插惨烈屠杀场面的具体细节[10][16]。1995年,香港导演牟敦芾拍摄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同样以纪实手法为主,这也是目前同题材电影中最为直观表现血腥、暴力场景的一部作品[10]。

到了90年代的《南京1937》,我们会发现创作者的思考重点已经不只停留在屠杀的血腥和残暴,而是以其为故事背景,将主题延伸至战争中的人性和救赎等问题[10]。
比如影片中成贤和理惠子组成的中日家庭,就在一个十分不寻常的设定中将普通的日本民众和屠戮无度的日本军人区别开来;到处掠杀的士兵得知理惠子来自日本后,顿时变得温和有礼,和《南京照相馆》的伊藤轻蔑表示“中国人的照片不重要”异曲同工[10]。这些细节都让战争中“人”的形象变得立体丰富:战场屠杀已经足够残忍可怖,但在多层次对人而非战争机器的塑造中,这种基于身份的区别对待更见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让普通中国民众在战争中的绝望处境显得愈发触目惊心。
可以说,《南京1937》拓宽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表达边界。后续的《五月八月》《拉贝日记》《南京!南京!》等影片在主题、人物形象、视觉表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通过儿童的眼睛看待屠杀对个体家庭的创伤;以日本士兵的视角反思战争,表达废墟之上的个体觉醒;四处围起的铁丝网、横亘的木栏杆,人群被限制在狭小封闭空间内的构图设计,显现的是面对屠杀的绝望[10][12][13]。研究这一题材的学者曾指出,因为本身就具有特殊性,相比消费民族灾难与创伤,影像更应该承担的是传递对历史、战争、生命等深层的思考[13]。
其中,“距离感”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和探索的内容。
拉贝先生在日记中提到:“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13]。”女性遭受的凌辱,是南京暴行中触目惊心的重要部分。为了反应历史真实,几乎所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都有对女性侵害的再现[13]。然而《南京照相馆》却没有将镜头对准受害女性,观众们记住的不是被侮辱和损害的痛苦过程,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侵犯者的荒淫无度和丑恶嘴脸之上,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女性处境的深切共情。

这种“拉开距离”的处理方式,正是许多优秀战争题材电影的共性。
《美丽人生》中,被枪抵着后背的父亲做出滑稽的鬼脸,用善意的谎言将儿子和战争的恐怖隔离开,枪声响起时观众反而更能感受到生命逝去的沉重。《万湖会议》则完整再现了艾希曼撰写的会议记录,正是这种有序平静的表象与背后千万生命毁灭形成的强烈反差,让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到罪恶的可怖。
研究者认为,对大屠杀暴力的影像呈现同样需要保持克制和距离感,更关键的是不要遮蔽历史中鲜活的个体生命。从宏大的全景展现,到照相馆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这正是这些年来电影人持续探索的方向,也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重要转变。
战争带给普通人的,是什么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摄影机对准的是铁丝网两边的稚嫩孩童,赤诚单纯的友谊在战争面前显得奢侈又珍贵,鲜明对比之下,观众在面对影片结尾男孩的死亡时也更加难以接受。《钢琴家》的故事里,人们跟随主人公颠沛流离的逃亡历程,能深刻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残酷与恐怖。
这些,就是历史的大幕落在普通人身上的重量。
《南京照相馆》的切入角度也是如此。平凡的邮递员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他走过的路是千千万万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路线;林毓秀怀着演员梦,为自己和大明星胡蝶的瞬间同框骄傲不已;开照相馆的老金刀子嘴豆腐心,你可以代入任何热情中不失原则的生意人。

观影时,30万人不是教科书上的数字,而是活生生个体的嬉笑怒骂、柴米油盐。所以面对战争、屠杀、凌辱,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真实和深刻的感受之一,是恐惧。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记录了一位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目睹屠杀场面的感受:“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到城墙外,鲜血四溅。这种阴森的气氛不仅让人毛骨悚然、四肢发抖[14]。”电影《屠城血证》中主角展涛为护卫照片表现出的无所畏惧,即使没有电影艺术的加工,也到底是极少数[15]。普通的中国百姓在现实威胁中,更多处于日夜惶恐不安的状态,以致于不敢外出取水[14]。
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研究者指出,人在面对危险和刺激时身体会进入警戒模式,甚至忽略饥饿、劳累与疼痛来全力应对危机。然而一旦情况糟糕到抵抗和逃脱都没有效果,那么人的自我防御系统就会被彻底击垮,产生无助、恐惧、绝望的感觉[16]。
毫无疑问,让千万人面对暴力和死亡处境的南京大屠杀,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创伤事件[16]。电影故事的具体设计,也必定会涉及到创伤性叙事的内容。《南京照相馆》选择的方式,是勾勒恐惧绝望的灾难中迫切想要“活下去”的真实欲望。
因此观众会看到汉奸王广海(王传君饰)为了获得出城通行证、为了自保,在日本军官面前毕恭毕敬。作为一个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普通市民,苏柳昌同样是懦弱怕死的。出于保命的考虑,林毓秀也没有拒绝为日本军官唱戏。
与此同时,这些角色却都不是脸谱化的纸片人。正如演员郝蕾所说“坏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王广海也打心眼里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背叛,反而因为没有拆穿苏柳昌的真实身份而将自己视为英雄。但当毓秀被拖进房间时,他起初呆愣住视而不见,最终却因为人性良知和愤怒放手一搏、挺身而出。
在死亡逼近、命悬一线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反而更会看到一个小人物立体多面的形象。

《南京照相馆》并不是一部毫无瑕疵的电影,观众能够从中找到不少情节不够合理、逻辑有漏洞之处,情感的转折也略显生硬。但它做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将故事交给普通人来讲。研究者提出,只有将大屠杀整体的抽象化与宏大叙事转化为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才能够真正走进在其中受难的人们[13]。
电影结尾,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观众看到了曾经在照相馆留下人生重要瞬间的年轻人、老人、孩子们的影像记录。镜头一转,他们在屠杀中备受折磨,惨遭杀害。而这些人,本应继续求学、工作、行医、参军,拥有完整的人生。
而能还原这样的复杂情感,或许也是《南京照相馆》“爆”了的原因。
作者:火火
内容编辑:火火
图片编辑:雪王
审核编辑:冷面
参考文献:
[1]界面新闻. (2025). 2025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破70亿元,《南京照相馆》大超预期.
[2]猫眼专业版.(2025). 2025暑期档期总票房.
[3]豆瓣电影. (2025). 南京照相馆.
[4]今日影评Mtalk. (2025).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背后的分量——对话《南京照相馆》编剧张珂.
[5]乌鸦预告片.(2025).点映口碑大爆!1:1揭露日军暴行!《南京照相馆》制作特辑,像素级还原场景细节.
[6]经盛鸿,方占红 & 武宇红.(2009).战时日本报刊新闻图片掩饰南京大屠杀.档案与建设,(12),39-40.
[7]笠原十九司 & 芦鹏.(2017).日本政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居心暴露于世——关于《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问题.日本侵华史研究,(01),126-133+139.
[8]何建明. (2023). 南京大屠杀. 中译出版社.
[9]严海建. (2022).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王霞. (2022). 历史语境与电影生产: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记忆变迁. 电影文学. 2: 99-105.
[11]南京日报. (2005). 《屠城血证》主人公原型逝世.
[12]万子菁. (2015). 另一个世界——战争电影影像造型研究. 当代电影. 8: 53-58.
[13]王霞. (2020). 视觉文化时代“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呈现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6: 149-153.
[14]张纯如. (2013). 南京大屠杀. 谭春霞,焦国林译. 中信出版集团.
[15]王霞. (2021). 诗与真: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3): 100-109.
[16]王霞.(2021).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创伤呈现. 电影文学. 2: 39-44.
作者:火火
配资公司介绍,网上配资网,国内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